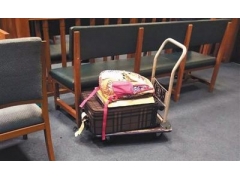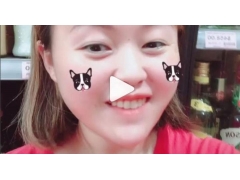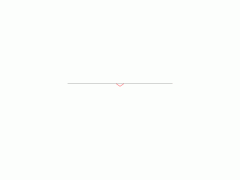切尔诺贝利,往事并不如烟

每年的4月26日,斯塔尼斯拉夫的思绪都会回到1986年的那一天,回到切尔诺贝利,那座曾经喧闹繁华,现在却已沉寂荒芜的城市。那场震惊世界的核事故已经过去32年了,但在他心里从来不曾忘记。

总编辑说,我是不会派你去的
1986年4月26日凌晨,核电站事故爆发的时候,当时身为苏联《劳动报》驻乌克兰首席记者的斯塔尼斯拉夫正在莫斯科开往基辅的火车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那时候他什么都没听说,消息完全是封锁的。等到了基辅就开始听到了各种传闻,小道消息已经私下散播了,但官方消息却始终没有踪影。26日中午11点,苏联政府应急临时委员会成立了。但还是什么消息也没有。他当即给认识的苏共乌克兰中央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办公室打电话,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方回答,发生了一场事故,一场严重的事故。作为记者,他说他开始坐不住了,“消息不断涌来,人们需要真相。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报道真相”。

斯坦尼斯拉夫·普罗卡普丘克
4月27日,他想也没多想,就给莫斯科的《劳动报》总编辑巴塔波夫打电话说要去切尔诺贝利采访,“明天我就可以发稿子,你们很快就能登出来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斯塔尼斯拉夫很感慨,“巴塔波夫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个大好人。他在电话里说对我坚决地说,‘我是不会派你去的’。他那时候应该是已经知道了一些真相的”。尽管总编辑反对,但他还是去了。他说,“我根本没想太多。那时候大家根本不知道核辐射是怎么一回事,完全不清楚是否会对身体产生影响。我也顾不得总编辑的反对了,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去,因为我是记者”。
摄影记者什么也没拍出来

1986年4月27日下午,普里皮亚季市与切尔诺贝利市所有53000名居民已由苏联政府安排的1000辆大客车全部撤出了。4月28日,政府开始疏散距离核电站1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其他居民。当天,斯坦尼斯拉夫与其他几位记者乘车赶往切尔诺贝利。当时除了斯坦尼斯拉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还有其他几名文字记者、摄影记者、电视记者,以及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斯塔尼斯拉夫和同行们坐车向事故区驶去,与此同时,更多的疏散车辆则以相反的方向载着人们逃离。“一路上就看到那些农民院子里养的牛、羊,甚至狗,都在茫然地看着路上往来的车辆。被疏散的居民被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拾出一个随身小包带着乘车离开。房子、田地,晾晒着衣服的院子,以及院子里的牲口、宠物,它们并不知道已经被人放弃了,只是茫然地看着比往日繁忙了许多的公路“,斯坦尼斯拉夫说。
“接近切尔诺贝利的时候,开始觉得有些异样了,嘴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金属味道。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但同车的人都感觉到了”,斯坦尼斯拉夫回忆起这一场景的时候用手指擦了擦嘴唇,大概就像他当年做的一样。一到目的地,他马上就开始采访现场的苏联防化部队士兵、从亚美尼亚调来开挖坑道的矿工、乌克兰当地征召的民兵,以及始终坚持在事故现场的核电站工作人员......斯坦尼斯拉夫说,“我是文字记者还好些,写稿子就可以。但摄影记者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核心区拍出来的照片后来冲出来都是一片空白,后来才知道是辐射的原因”。”关于核辐射,大家都没有经验,刚开始冲到第一线的人们连基本的防护措施都没有,有些部队甚至是以军事演习的名义被调过来的。那些小伙子们还以为是要来扑灭一场普通的火灾。那些年轻人啊,就像一颗颗的肉丸子......”
切尔诺贝利并没有死去

斯塔尼斯拉夫说,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后,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皮肤开始脱皮,就像被晒伤了一样,一层一层地脱落下来。后来又有些其他的疾病,都和辐射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但他并不愿多谈。他说,比起那些牺牲的人,他已经很幸运了。据乌克兰官方2006年的统计,有大约240万的乌克兰人(包括42.8万名儿童)受到这次事故的辐射影响,导致出现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人类的健康问题主要受放射性物质“碘-131”所影响。而锶-90和铯-137对土壤造成污染更为持久,植物、昆虫和蘑菇会从土壤中吸收铯-137,并将受污染的食物呈现在人类的餐桌上。所以,有些科学家担心核辐射会对当地人造成几个世纪的影响。
当年发生爆炸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核反应堆在事故发生后被建造的混凝土“石棺”封闭起来了。但斯坦尼斯拉夫表示,“石棺”或“坟墓”这样的形容并不准确,切尔诺贝利的核幽灵并未死去,只是在沉睡。据官方估计,反应堆内还有大约95%的燃料(约180吨),这批燃料的总放射性高达约1800万居里。尽管残留在内的放射性物质已经硬化成陶瓷状物质,但随着“石棺”的风化老化,随时存在释出后辐射扩散的问题。2016年末,一座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赞助建造的高105米,长150米,宽257米的新一代“石棺”,预计将于2018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新“石棺”将可以运行100年。一百年后,核辐射的幽灵会不会跳出来,或许到时人类会有更高的智慧去降伏它。
放在现在,结果恐怕很难预料

谈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启示,斯坦尼斯拉夫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始缓缓地说,“尽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无数人的生命还是被挽救了。如果有什么启示,那就是幸亏是在苏联时代,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指挥调动,能源源不断地将人和资源输送过来,不惜一切代价去挽救生命,不惜一切代价去扑灭灾难。我想,如果放在现在,结果恐怕很难预料”。1986与1987两年,苏联政府征调了24万人参加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现场抢险工作。至1986年12月,苏联政府在4号反应堆上建成了“石棺”,封闭住事故现场。总计有60万苏联人获得了切尔诺贝利事故抢险奖章与勋章。
1987年,因“在切尔诺贝利事故报道中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技巧”,斯塔尼斯拉夫·普罗卡普丘克获得了苏联颁给记者的最高荣誉“金笔奖”。当时获得这一荣誉的全苏联总共只有32人,但斯坦尼斯拉夫对获奖的话题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说,“当时只有塔斯社可以发官方消息。我虽然4月28号就到了现场,但发回的报道一直被压到5月11日才见报。其实当时那样的新闻管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很多第一时间冲到现场的记者只是想尽快把真相告诉大家,但我们没有做到”。1986至1987年间先后参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报道的记者组建了一个“切尔诺贝利记者联合会”的组织,有上百人的规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疾病等辐射后遗症的困扰,斯塔尼斯拉夫说,“当年的同行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基辅市总共也不到10个人了”。
每年4月份,他都会想起1986年的那个4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说他也在写一篇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文章,准备4月26日见报。他还是那句话,“因为我是记者,我是从现场回来的记者”。
今年的这个4月,基辅桃红柳绿,尽管少有人提起,但在斯坦尼斯拉夫和很多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的心里,那一年那一天的切尔诺贝利,一切从来不曾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