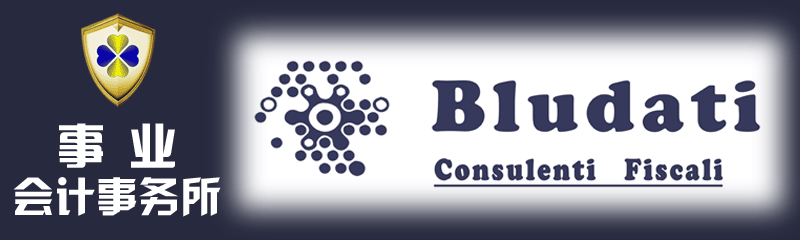“塔尖接棒”的企二代:多数不愿接班远离制造业(图)(2)
2012年,按赵照的高考分数,他只能将就进一所大专。于是,不愿复读的他被父母送去美国念商科。这个小伙子后来在波士顿养着一条狗、一辆玛莎拉蒂。在旁人眼里是一个标准富二代,花钱大手大脚,学习不上心。今年8月之前,他从没有考虑过接不接班,更不用提什么危机感,他甚至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今年暑假赵照回国,他发现父亲突然有了中年危机,不时会趁赵照在家时找他促膝谈心,父亲主动提起2008年触目惊心的倒闭潮和2010年不堪回首的担保风波,提醒儿子要培养敏锐的商业嗅觉,以及“关系再好,也坚决不给对方担保。”聊的最多的则是2012年的借贷危机和自己的卑躬屈膝。
原来就在他出国那年,父亲的工厂正处在痛苦的转型期。
据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凌介绍,从2012年上半年,浙江企业的减产迹象就日渐显现,尤其是在浙江企业生产效益经历了20%~30%的高增长之后,骤然放缓的增长对企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而一些行业就完成了重新洗牌。而家族企业传承的一大难题是,“理解家族传承的大环境背景,如代际传承就好比一场政变,可能降低企业的存活率。”
后来,工厂从原来生产洁具(例如花洒)转型到无污染暖气片,需要花2000多万从德国和意大利进口整套流水线,这一度让赵照的父亲抓耳挠腮。“做我们这种企业的一般现金很少,都是举债经验,有收益再投入生产升级。但那时向银行贷款很难,跑断了腿也没用,就是不贷给你。”父亲只能跪求亲戚,最后有亲戚同意用自己的房产证作抵押,银行才放贷。
赵照从心里佩服父亲独自撑过那么一段日子。
他注意到,近年父亲抽烟变多,即便跟他聊天时都不由自主点上烟,聊两个小时,烟灰缸里已满是烟蒂。两鬓斑白的父亲逗趣说,戒烟的议程只能摆在退休后了。他知道,父亲暗示的无非是自己需要有接班的心,不能再吊儿郎当下去。
父亲原来经常跟赵照说,企业光靠一代是不够的。但当初赵照没把这话往心里去,他认为“管工厂太苦了,爸爸要熟悉每一道制作工序,但方方面面都要盯着,把自己累趴也不一定能管好。”
而在大学参与外企实践时,他观察到现代化企业当中人与人的“信任半径”是很大的,不需要总裁事必躬亲。
之前,他连父亲厂里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但今年暑假结束回波士顿之前,他多次去父亲的厂里调研。当初帮助父亲借贷度过危机的亲戚虽然早已“退出朝政”,但他很快发现了父亲亲力亲为的原因。比如亲戚有个不务正业的儿子被安插在厂里,无所事事。
在陈凌看来,家族传承涉及到的难题还在于如何将社会组织管理(家庭)和经济组织管理(企业)进行有机结合。
“将来即使接班,父亲肯定也会处理好这些问题再交给我。”但他也同时明白,如果父亲狠不下心变革,那下狠手的可能是自己。当提及“元老阻力”,赵照显出泰然,“家族企业里,元老不一定就是阻力,还是看人,”他说,厂里有个老会计跟着干了20多年,亲历企业走过难关,兢兢业业,从不言弃。
他觉得由奢入俭难,与其入俭,不如先让自己口袋鼓起来,以后也可以不再问家里要钱,毕业回国后帮父亲开拓海外市场。
创二代:分家用“口袋理论”,电商救传统制造
陈凌在此前的调研中发现,中国的家族企业在继任问题上,很少像西方的家族企业那样,在第二代采取兄弟姐妹合伙经营模式,而是将企业传给一个子女,然后资助其他子女创建新的公司,并建立一种互动的网络关系。
相较90后的年轻一辈,70后刘子阳当年的想法显得保守。刘子阳虽曾抱着旧思路去市场中试错,可最终还是听从父亲的建议回工厂帮忙、学习。终究他因“分家”难局离开老厂,但一直遵循着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延伸贸易,做起了跨境电商。
1999年,22岁的刘子阳大学毕业,浑身都是劲,他的父亲做暖风机起家,辉煌时年销售额过亿。“不管是去做接班人也好,或者是在一代的基础上自己去再创业也好,当时都有一种创业的心态。”
刘子阳描述当时的心理,“总觉得父亲的企业终究是父亲的,急需做出些成绩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
于是一毕业他就“头脑一热”进入完全陌生的服装业,借父亲的资金开了针织厂,没开多久就发现产品完全滞销。“满脑子都是有货就有市场,到我们真正进入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已经早过了70年代供远小于求的红利期。
于是,他只能灰溜溜回到父亲的厂帮忙。他的姐姐、姐夫比他早两年进入父亲的企业,主做外贸,而他入厂则被安排负责内销。没有网购的年代,小家电早期的经营路径很粗放,占领商场,而且是一线城市的商场。刘子阳说,“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做品牌,只会打价格战杀红眼,后来就收到同行恶意投诉,说我们坏了行业规矩,人家卖199的,你卖99,搞得大家都没饭吃。”
被同行“打击”后,他却意外发现了那时并不流行却具有规模效应的电商渠道,“随便一上去就100多万订单,于是我就把所有精力都放到电商来。”但这一做,牵出了与姐姐之间的矛盾,电商不分内销外贸,一定程度上瓜分了属于姐姐的利益。“大家都涉及外贸业务,一些客户重合,客户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很快导致了2003年的分厂,父亲决定将儿子和女儿的利益分开。
2006年,刘子阳在第一期家业长青的班上听方太集团创始人,宁波家业长青学院院长茅理翔说“口袋论”——“就是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一个口袋的人具有相同的利益,可以一起经营。”
刘子阳和姐姐至此已变成了两个口袋。“分家”常被认为是家族财产的积累性差,导致“富不过三代”。
刘子阳很快面对两亿多销售额的瓶颈,“瓜分了66%市场后,销售额再也做不上去了。”到2007年,他搬离老厂所在的新浦镇,到30公里远的慈溪市中心租了写字楼专做创意家电的电商。在此过程中,他重新和姐姐成为上下游的关系,类似渠道商和供应商,互相扶持。
将入不惑的刘子阳有一双儿女,面对着江河日下的制造业和前途未卜的电商,他希望孩子未来能懂一些金融和资本运作,逃离传统制造业。
家业长青创始人:淡化家族制,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刘子阳毕业那年,抱着拳拳之心投入市场,年近花甲的茅理翔则跪在老母亲面前,老母亲哭着骂他是不孝子孙,富了便忘了亲兄弟。
茅理翔的四弟原是一个小厂的厂长,厂子倒闭后想进方太集团的管理层。茅理翔身为公司董事长,儿子茅忠群是公司总经理,满足弟弟的要求似乎不难,但他没有同意。
此前,茅理翔就已提出,家族企业的管理要淡化家族制,方太集团高层干部不准有自己的亲戚或者家属成员。当时,他要为儿子茅忠群接班绸缪,也为企业发展着想。
然而,这套理论跟老母亲是讲不通的。
茅理翔跪了10分钟,这一跪,成了茅氏家族企业传承与转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06年,66岁茅理翔创办家业长青学院,几乎免费给企业的二代进行培训。
同年,他从方太的管理层退出,由儿子接棒,他则自豪宣布“大胆交、彻底交、放心交”,消除外界对他可能“垂帘听政”的疑虑。
老先生初见生人时喜欢跟人握一握手。尽管视力衰退得厉害,他由两位助理引导还是跟记者握上了手。76岁的他还是很忙,坚持每个工作日去公司,给交接班的企业做辅导咨询,同时收集案例供后来者研究。每周和儿女吃一顿饭,谈论工作;周末陪孙子下一场棋,教他博弈。
他也因为退休后办校讲课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他遇到过痛苦的“创一代”,子女有的不争气不能接班,有的叛逆独立不想接班。他也遇到过郁闷的二代,有个二代从天津开着奔驰车去北京接他,见面聊了几句便说,“我爸爸像你这么开明开放就好了。”
还有个45岁的二代,进企业五年了,说“父亲什么都不教我,也不肯放权。”
茅理翔跑去问二代的父亲,“你为什么不交权?”
他说,“王永庆到89岁才交权,我才73岁,还是小弟弟呢。”
而两代人之间相处多数情况是——见面不说话,说话就吵架,吵架就离家。
在茅理翔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诞生了上千万家的家族企业。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从世界经验来看,第一代到第二代成功传承的比例只有30%,如果以每年200万家消亡为周期的话,结果令人忧心。”
于是他开始总结传承中所面临的难题,包括“舆论压力”、“家族成堆”、“元老阻力”、“兄弟纷争”、“父子分歧”、“宏观危机”等十多个。他也有意在这些传承问题前加上“中国特色”四字,中国家族企业的特点是“创业初期很团结很有活力,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排斥人才,往往情份第一,制度规则放旁边。”“所以我提出了三治模式,以法治为主,德治和情治为辅,比如党建文化、儒家文化、传统情感三者相辅相成。”
2009年5月,杭州发生富二代“70码”飙车事件。一时,许多二代们向茅理翔倾诉迷茫,有些二代留学回国后本来雄心勃勃继承家业,回国后却发现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将富二代说成“坏二代”、“败二代”,甚至仇富蔓延,内心顿生犹豫挣扎。
2010年9月天津达沃斯分论坛,茅理翔做演讲,“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改变人家的想法,首先要改变自己的做法,把自己 富 的帽子先摘掉,带上一个 创 的帽子。”很快,这股风首先吹到慈溪庵东镇上,2010年的尾声出现了全国第一个镇级创二代联谊会,主要由家业长青班06级第一期学员们联合当地的部分企二代一同组织成立。接着是2011年6月16日慈溪市工商联牵头成立市创二代联谊会,到2013年1月20日,浙江省新生代联谊会也宣告成立。
“目前在管理学里还找不到一个传承学的理论,以后能开设FMBA(Family MBA 家族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就好了。”茅理翔因此投资了两千万成立浙江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
在茅理翔看来,创二代责任非常大,他们所承担的不光是接班,同时也在经受转型升级挑战,大多数传统家族企业可能面对生死存亡的问题。创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不仅仅是某个家族的事,某个企业的事,而是一个国家的大事。
而无论“塔尖交棒”或“另辟蹊径”,继承者们的选择将会影响到一座城,乃至一个行业的兴衰更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